内斗的极致
cn·@ancient-light·
0.000 HBD内斗的极致
1980年代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是:**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,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**。对中国人内斗危害之重,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表达了。下文中的一些内斗事例,颇具典型性,尽显那个时代的官场生态。这些事例涉及河南、安徽、山东,它们属于大饥荒年代的5大重灾区(另外两个是四川、甘肃)。内斗与饥荒相连,这不顺理成章吗? ### 吴芝圃pk潘复生 官场以外的人,虽不至于天真地以为官场同僚精诚团结、亲如兄弟,但也不至于想象成势如水火、你死我活。然而不幸的是,后者或许更是事实。 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涉及两位官员:吴芝圃与潘复生,大跃进初期分别官居河南省委第二把手与第一把手。 吴芝圃(1906—1967),  河南杞县人。此人并无忧天情怀,倒是将河南折腾得天翻地覆,其中的重头戏就是与潘复生合演的双头斗。 潘复生(1908—1980),山东文登人。本文无意全面评价此两人的功过是非,只关注他们的官场折冲。  在中国官场中,吴潘两人的官阶决定了,吴绝对应听从潘,没有任何争辩余地。但在1957年12月的河南省党代会上,吴芝圃似乎奇迹般地颠覆了多年以来的官场规则,奋起批判潘复生的“严重右倾错误”。并非吴芝圃特别胆大,敢于以下克上,而是他的后面站着副总理谭震林,而谭震林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。 那时最高领袖正在筹划大跃进,而河南的两大员,潘偏右吴偏左,领袖早已看在眼中。消息灵通的吴芝圃见机而起,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在那个疯狂年代,偏右于国是很高的德行,而于己则是极大的风险。 一号政治上失势,二号乘机而上,取而代之,这种事在中国官场并不足怪,也谈不上失德。但吴芝圃继续落井下石,穷追猛打,下手特狠,就不免过头了。 1958年5月,北京的中央会议作出了吴上潘下的决定。会议还没有结束,吴芝圃就强烈要求将因病住院的潘拉出来批斗。会后,立即将潘从北京楸回河南批斗。吴芝圃一回河南就召开省委全会,主题就是“批判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”,通过了《彻底揭发潘……反党集团的决议》。吴本人在大会上公开号召:对潘复生“要斗透,从政治上、思想上揭发,要反复斗争”。会后紧随而来的批潘运动声势之大,火力之猛,就是在那个内斗盛行的年代,也属罕见。河南全省抓的“小潘复生”,竟有20万之多,其中厅局级干部18人;批潘的“大字报”达十几亿张。这种架势,在局外人或后世人看来,绝对是不可理解的人世奇观! 吴芝圃对于已经“落井”的昔日上级,在政治绞杀中的种种狠招,难以尽述。无论从官方公开申言的政治道德、自古以来士大夫信守不渝的传统道德,还是出于人之常情的民间道德,吴芝圃都找不到替自己行为贴金的理由。而且,吴芝圃正是乘批潘的势头,在河南掀起不顾民众死活的大跃进,最终以数百万饥民生命的代价,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句号。 据说,吴也是饱学之士,每次去地县巡视,居然也学老人家,总不忘带一大篓子线装书。或许他只是附庸风雅,但总读过一些古今贤哲的书,不会不知道败德背义的行为,最终将逃不过历史的仲裁。一个在内斗中不择手段而又失政害民的人,他将在史册中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? 我们的故事中的这两位主人公,后来命运都不佳。 吴芝圃在河南铸成大饥荒,1962年免职后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;文革中遭批斗,郁郁而终。潘复生1958年撤职后下放农场劳动;1962年平反,任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;1966年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;文革中犯“极左”错误,文革后被整肃,案子至1980年去世时仍未了结。 ### 曾希圣pk张启帆 一个颇为灵验的规律是:在战争年代敢斗敢闯的人,到了和平年代的地方官任上,多半也是勤于折腾、不惮于闹个翻江倒海的狠角。曾希圣正是这样的人。 曾希圣(1904—1968),  湖南资兴人,战争年代他是毛的爱将,1950年代主政安徽,风格激进,深得主公赏识;只是直至将个好端端的安徽,硬是折腾成全国闻名的重灾区,让几乎500万饥民成为饿殍,才在1962年黯然下台。曾希圣视政坛如战场,长于政治角斗,不忌惮排除异己,整人无数,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张恺帆。 张恺帆(1908—1991),安徽无为人,大跃进年代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与常务副省长,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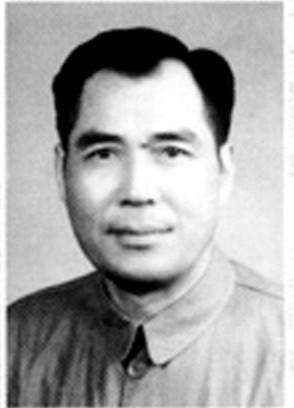 是曾希圣的主要副手之一。张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,早年师从有气节、讲操守的乡绅学者,自幼得到抑强扶弱、救世爱民一类传统观念的熏陶,并不情愿做一个泯灭良知、残民以逞的无德官僚。 这样一个人,在那个昏天黑地的大跃进年代,如何能够既洁身自好、又不损官运?其遭遇不测几乎不可避免。张恺帆的受难地不在别处,正在他的故乡无为。 无为是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,但在1959年却成为特重灾区,损失了近1/3的人口,人祸之惨烈,莫此为甚!风闻无为大事不好的张恺帆,匆匆赶去调查,他所看到的真正是“千村薜荔人遗矢,万户萧疏鬼唱歌”,老乡们在他面前下跪,直呼“省长救命”! 面对此情此景,张恺帆还有何话可说,只是救民而已。他立即下令:停止上调粮食,足额发放口粮,解散公共食堂,开放集市贸易……。这就从鬼门关拉回了无数生灵,却不曾想,自己已经陷入了险风恶浪。 原来,曾希圣的心腹已将张恺帆的所作所为记录在案,火速上报了正在庐山开会的上峰。最高领袖立即对此事定了性:张恺帆是“彭德怀、高饶的余党”。敌人就在眼前,曾希圣等人岂能不闻风而动?由庐山直接指挥的批张运动就此迅速展开。 对一个钦定罪人布置批斗,自然是曾希圣分内之事,没有人能苛求他放过张恺帆。问题在于,对于自己知根知底的这个主要副手,而且还是多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,曾希圣不免下手太狠了,远远超过了寻常道德与情义的底线。 在曾的直接指挥下,将张恺帆连续批斗了51天,关押审讯了200多天,最后开除党籍,流放到矿山服苦役。从批斗张开始,张的一家就被扫地出门,押到淮北一个林场劳改;与案情完全无关、原为新四军老战士的妻子,在流放地吃尽苦头,几至双目失明。张的亲朋故旧也受到株连,有6人被迫害致死。株连还波及无为的近3万普通民众、干部。 仅仅因为救灾民于水火,就使自己、家人、故旧及民众蒙受如此大难,这大概是张恺帆始料未及的。尽管如此,“张青天”之名还是不胫而走。不过,在那个荒唐年代,民意顶个屁用! 曾希圣1962年被调职,并被追究在安徽的失职。此后淡出政坛,文革中未免整肃。张恺帆1962年被解除处分,此后直至1980年代,一直在安徽任职,官声颇佳。晚年热心于文化活动,有诗集传世。这是一个“好人自有后福”的稀有例子。 ### 舒同pk赵健民 下一个故事转到了山东。齐鲁大地原是“礼乐之邦”中的礼义之乡,它能容得下违情背礼的内斗吗?好家伙!内斗的大戏照演不误。孔夫子也得过阶级斗争关,不斗行吗? 这次的主角唤作舒同、赵健民,分别官拜山东省委书记与省长。 舒同(1905—1998),江西东乡人,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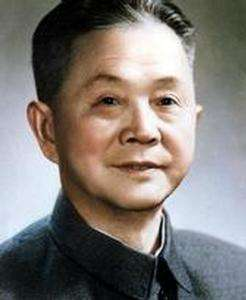 自井冈山时代起,就是毛泽东的亲近追随者。舒同半生戎马半生官宦,最终竟主要以书法家之名行世,而且并不是捧出的虚名,他独创的“舒体”已具相当影响,成为今日电脑中的重要字体。这也算是现代史上一件趣闻。 或许正因为如此,舒同一生都生活在他练字时达到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幻境中,从未立足于真实的现实土壤。他战争年代仅涉政治宣传工作,并不亲手行兵布阵,似无大碍。和平时期一旦作为地方诸侯独当一面,又不能充分信用手下才俊,刚愎自用,就不免闹出许多笑话;再加上紧追主公的浪漫狂想,那就更加不可收拾。 大跃进期间的山东乱局,已荒唐得十分了得,一个自古富庶之地,竟至活活饿死人无数!而舒同多少年之后心中仍然不甚了了,只是说“被别人骗了”而已,岂非十足的痴话? 就是说痴话,也解释不了与赵健民的二人斗。 赵健民(1912—2012),山东冠县人,  1955至1958年任山东省长,成为舒同的主要副手。赵健民长期在山东生活、学习与工作,战争年代既当司令又当政委,和平年代既当书记又当行政主官,对于地方事务自然有较实际的经验,而这与舒同那种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,不免有很大的反差。舒同在处理人事与政务时,似乎仍然如他写草书般的天马行空,浪漫飘忽,这就使赵健民这个省长越来越难当了。最高领袖站在哪一边,是不言而喻的,赵健民的命运也就决定下来了。 两位主官政见不一,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不稀罕,通常也不缺乏平和的破解之道。但唯有毛所倡导的办法最具有独创性,那就是用“阶级斗争”来解决,即“正确路线”一方斗倒“错误路线”一方,当然,“正确”得由权力说了算。 舒同与赵健民之间的这笔账,终于在1958年夏天清算了。赵健民埋头政务,并不知道大祸临头;而舒同则似乎已经盘算定当,成竹在胸。 6月,舒同主持省委会议,集中批判赵健民,罪名是地方主义、分散主义、宗派主义,这些名词今天人们已经十分陌生。不过,舒同说的大白话,倒是点出了问题的实质。舒同批判赵健民: “无非是要把省委搞掉,由健民同志取而代之”。赵健民是否想取代舒同,我们不得而知;但舒同真正在意的就是这个:任何人不得夺了他的大位!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,都不过是表面文章,权力才是真正的命根子。 本来,文明社会中的权力博弈并不稀罕。但像舒同那样完全变成赤裸裸的叫板,变成贩夫走卒式的争夺,不讲任何规则与修饰,也只有在毛时代的中国官场才能看到。既然一切都以组织的名义安排好了,赵健民哪里还有招架之功?唯有缴械投降了。1959年2月,山东省作出了对赵健民的处分决定,将赵贬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去了。 只要出现分歧,就一概指斥持异议者有野心、想夺取,并以“反党”罪将其打倒,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恶劣的传统,它不仅制造冤案无数,而且使官场一片萧杀、了无生气。 这场内斗的两个主角后来的命运都不平坦。舒同1961年因大饥荒的责任被撤销山东省委书记职务;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;文革期间一度被拉回山东批斗,此后遭长期监禁;1979年获平反,历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、全国政协常委等职。 赵健民1962年获平反,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;1968年被康生诬为叛徒,入狱8年之久;文革后获平反,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;晚年热心于参与政治民主化、反腐方面的学术讨论。舒赵两人堪称长寿,应不乏会面机会。倘在晤谈中共同忆及当年旧事,不知他们会有何感慨? ### 不斗行吗? 上述故事中的6位主要人物,命运或有差异,功过或有高下,但都是内斗中的失败者,谁也没有从内斗中得到什么东西;即使一时得分,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。实际上,内斗给了每个人的身心以沉重的打击,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元气。 岂止是这6个人,在中国所有陷入内斗的人,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,都难逃脱类似的命运。这就不能不说,对于中国社会——首先是官场——内斗是真正的祸害,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孽。 于是自然要问:不斗行吗? 在疑惑之际,你可能恰好听到一个伟大的声音飘然而至: **中国有8亿人口,不斗行吗?** 我真不知道此话的逻辑何在,为什么有8亿人就一定得斗,今天14亿人了岂不更要斗个天翻地覆?或许,可能的理由之一是: 任何群体(包括组织、机构、政府)难免不同声音,这就有碍于一致行动。 破解此困局有两条路径:用程序化方法作出选择;或者强势者压服弱势者,令其闭嘴服软。第一种方法需要完善的规则与组织构架,费时费事。第二种方法看起来颇为不雅,但简单方便,一定会有一些人大呼痛快。要对手闭嘴,非内斗别无选择。 现在,你应当已经明白:不斗行吗?显然,只是对于接受第二种方法的人,上述理由才说得通。然而,既然已有那样多的事例说明内斗恶果累累,再坚持使用第二种方法,就匪夷所思了。为了避免内斗的恶果,值得付出一定的代价,这就是为运用第一种方法作必需的准备——那正是为建设一个现代法治社会所需要做的。 最后一层理由似乎说明了:不斗能行,而且应当力避内斗!
👍 let-it-fly, wuilgrey, taos, yjcps, bitok.xyz, justyy, lilypang22, dongfengman, ilovecoding, jianan, sweet-jenny8, steemfuckeos, dailychina, woolfe19861008, dailystats, turtlegraphics, witnesstools, laiyuehta, superbing, ethanlee, anxin, xiguang, francescak, doraemon, cnbuddy, shentrading, majack, fucktime, xiaoshancun, ancient-light,